媒体报道
生命“器”约(2024.01.04 北京日报)
本报记者 孙乐琪
移植手术,20世纪伟大的医学奇迹,也是人类生命最为特殊的延续。
从人面蛇身的女娲到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图腾崇拜中蕴含的移植思想在浩瀚的古文明中熠熠生辉,体现着人类对超凡生命力的原初渴望。人类对器官移植可能性的探讨,从古至今从未停止。战国时期,《列子·汤问》中就有“扁鹊换心”的寓言;而在公元前2世纪的古希腊,医学家皮吉罗斯就已经有过动物器官移植的尝试。
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到现代社会的医学突破,是什么让移植真正走进现实?北京友谊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儿童肝脏移植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朱志军认为,那应该是一代又一代医者出于对患者的悲悯,一次又一次的勇敢尝试。
将“死去”的生命以“活着”的形式留存在世界上——移植体现着人类崇高的互助品质,而捐献器官资源的紧缺迫使医者不断迎难而上、辟路前行。
从医25年,朱志军在一次次果断的两难抉择中,为重症患者解决肝源问题蹚出了一条新路。他带领团队首创的“多米诺交叉辅助肝移植”手术,甚至实现了不需要器官捐献的器官移植。

朱志军(右二)正在进行移植手术
放手一搏
“我考上大学了,9月就要到北师大珠海校区报到了。”去年7月,来自湖北省黄冈市的小严在父亲陪伴下找到朱志军的诊室。他不仅仅是利用暑假来复诊的,也是为了当面向看着他长大的、长辈般的“朱爸爸”报告考上大学的喜讯。
朱志军看着眼前18岁的小伙子充满生机的笑脸,感到了难以名状的巨大欣慰。17年前,那个曾令他感到艰难,而又无比幸运的场景,又浮现在他的脑海。
2006年,朱志军还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医师,出生后即胆道闭锁的小严在父母怀抱中四处求医,辗转来到朱志军面前时,已是1岁2个月大了。
胆道闭锁会造成新生儿胆汁淤积,救治不及时容易出现肝硬化、肝衰竭,严重者可危及生命。如果患儿已经出现肝衰竭或肝硬化、门脉高压失代偿,肝移植是唯一有效的根治手段。
此时,小严已经严重黄疸,出现了不可逆的胆汁性肝硬化。襁褓中的幼童,因消化道出血时而出现吐血症状,令见者无不心疼。各种指征都指向了唯一的答案——换肝。婴幼儿要通过器官捐献的途径获得匹配的肝源十分困难,为此,小严的父亲希望为孩子活体捐肝。
然而,当时全国尚无为3岁以下婴幼儿实施活体肝移植手术成功的先例,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此前也没有实施过活体肝移植手术。保证手术成功的同时,还要兼顾供者的安全健康,这是此前从未面临过的挑战,种种待解难题让朱志军踌躇不已。
但孩子的病等不了。此时的小严胆管炎反复发作,已出现了肝衰竭的症状,再不立即施救将有生命危险。朱志军反复权衡手中的“筹码”:虽然没有为这么小的孩子做过肝移植手术,但从医以来深耕领域多年的他已经有了近千例肝移植手术的成功案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流程十分熟练。同时,他也曾多次赴我国香港、台湾和日本、韩国等儿童肝移植技术成熟的医院进行观摩。
不手术,孩子命在须臾。为给孩子争取生机,朱志军决定放手一搏。
“虽然术前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预判手术难度较此前的病例都要大很多,但仍然没想到,实操要比想象的还难。”朱志军至今清楚记得,那天是2006年9月15日。清晨,移植外科、重症监护病房、麻醉科等科室的医护人员就紧张地进行术前准备,严阵以待。上午9时,朱志军领衔,手术正式开始。但这场手术却没有按惯例在当天16时左右结束。一场鏖战,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时长近18个小时。
稚嫩的婴儿,血管之细超出了朱志军的预判,动脉还没有一根牙签粗。而当时的手术设备和经验,并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和细致,“今天给婴幼儿做手术可以使用大倍数的放大镜,甚至显微镜。但当年,做这个手术时,我使用的仅为一个2.5倍的放大镜。”这就需要医生拥有特别纯熟的经验和加倍的专注力。
令朱志军印象深刻的是,那场手术,仅吻合患儿的动脉血管就花费了4个多小时。血管吻合后,当超声检查显示血流通畅,在场的每一名医护人员都松了一口气,朱志军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了下来:“最难的部分顺利完成,手术基本可以宣告成功了。”
17年过去了,如今小严已经成年。中国肝移植注册的数据显示,他保持着全国婴幼儿(3岁以下)肝移植最长的生存纪录。如果不是还需使用抗排异的免疫药物,你很难察觉出他与一名普通大学生有什么差别。
由于肝移植术后患者需定期随访,小严每年都会在寒暑假如约找到朱志军,一路从天津追随到了北京。“在长年紧密的联系与相处过程中,肝移植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关系往往就像家人一样密切。”朱志军说,这些年,他曾为因当地药品紧缺而有断药风险的小严多方联系、奔走,保证他免疫治疗的连续性。小严赴珠海求学后,因担心孩子路远奔波,他又帮忙联系上了当地有器官移植资质医院的专家,方便小严随访复诊。
十几年过去了,朱志军团队已为超800例患儿进行了肝移植手术。“孩子们小的时候都喊我‘朱爸爸’,长大了、腼腆了,就不好意思喊了。”朱志军笑着说,不论孩子们喊什么,他永远都会站在他们身后,为他们的生命和健康保驾护航。
重塑规则
世界肝移植之父、曾于1963年完成全球首例肝移植手术的美国器官移植专家斯塔齐尔有一句名言:“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说明肝移植手术对器官捐献的依赖性。由于捐献数量有限,要获得配型合适的肝源,患者往往需经历漫长的等待。
2018年12月29日,一场特别的手术在友谊医院肝移植中心顺利完成,两名患有不同遗传代谢缺陷肝病的患者互换半个肝脏,实现了不需要器官捐献的器官移植。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手术,主刀者正是朱志军。
那一年,友谊医院的病房住进两名分别患有两种罕见的遗传代谢性疾病的患者。8岁的周航患有高蛋氨酸血症,需要长期服用特殊食物,血中蛋氨酸血最高达每升1300微摩尔,头部核磁检查提示脑白质损伤,如果进一步发展可能出现智力减退及神经系统损害。19岁的邵勇同时患有OTCD(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乏症)和HHH(高鸟氨酸血症-高氨血症-高同型瓜氨酸尿症综合征),这导致他反复发作肝性脑病,即使严格限制蛋白饮食,也已经出现了脑损伤、语言障碍、运动障碍、肌张力高等严重的神经系统损害。
肝移植手术迫在眉睫,捐献肝源却尚无着落。如何才能延续生命,保全两个家庭的幸福?朱志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让两名患者互换部分肝脏,各取所需!
他查阅既往资料和研究成果,认为两名患者的代谢性疾病虽然均可导致神经系统损伤,但是病变存在于没有交叉的不同血管通路。加之两个人血型相同、肝脏形态差别不大,理论上,完全有可能通过互换两人的部分肝脏,来实现肝脏功能的完善。
而这个手术方案,并不是朱志军突发奇想的。为此,他已准备了近10年之久。
朱志军回忆起2009年的一次相关实践。当年,一对兄弟慕名找到朱志军,哥哥要给弟弟捐肝进行移植,但评估后发现哥哥的肝脏长得比例不合适——如果捐右半肝,则残肝不够自身使用;如果捐左半肝,又不够弟弟使用。保证供者的安全是做亲体器官捐献的最高原则,怎么办?两难的局面让一心救人的朱志军陷入了痛苦的思考。
当时,病房里刚好有一名8岁的遗传代谢病女孩马上要进行肝移植手术,即将切下来的肝脏除了草酸代谢异常以外,其他功能都正常。“如果把这个‘废弃’肝脏与哥哥捐的左半肝合用,能不能既防止出现亲体捐献肝脏过小带来的‘小肝综合征’,又辅助解决女孩肝脏的草酸代谢障碍,从而‘联手’发挥完整的作用?”思路清晰后,朱志军又进行了理论和技术上的推导,证明可行后实施了移植手术,并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以往成功的经验,给迷惘中的朱志军提供了“解题思路”:既然带有缺陷的肝脏可以通过辅助移植治疗,那它也可以作为辅助移植物来发挥其缺陷以外的功能。朱志军“互换肝脏”的想法获得了双方家属的认可和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他决定为两名患者互换左半肝来完成肝移植手术。
这是一台神奇的手术。不光是理论设想超前,在外科技术上更是要求极高。通过数字影像技术,朱志军带领团队构建了肝脏三维透视图像,精确计算了移植肝脏的大小以及两个肝脏上的每一条血管和胆管,确保手术万无一失。9个多小时后,两台肝移植手术取得了成功。术后,两名患者不仅代谢障碍得到了纠正,肝功能也基本恢复正常,很快顺利出院了。
在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朱志军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不同的非硬化代谢缺陷肝脏疾病患者之间,可以通过互换半个肝脏,而治愈各自的代谢缺陷。”他把这种手术命名为“多米诺交叉辅助肝移植”,而这次手术则是全世界首例“多米诺交叉辅助肝移植”。
这不仅仅是术式上的创新,更为重症肝病患者解决肝源问题开辟了一条新路,也为未来基因治疗代谢性肝病留下了空间。因此,它也被国际上誉为“重塑规则的术式”。
如今,5年过去了,当年互换了一半肝脏的两名患者怎么样了?“他们都长大了。”朱志军回答时,笑意里充满慈爱和欣慰。

朱志军(右一)与团队研讨病例
舍简就繁
“朱教授,感谢您4年前的果断手术,不仅挽救了我的生命,也使我拥有了现在的美好生活!”2023年3月,24岁的武敏专程来到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看望朱志军,道谢的同时,一并报喜:她结婚了。
2019年8月,武敏因急性肝衰陷入深度昏迷,入院时情况危急,已出现凝血功能衰竭和明显的脑水肿。幸运的是,救治团队当晚就通过国家器官分配共享系统匹配到了合适的肝脏。
急性肝衰的救治等不得,按照传统惯例,需要立即换掉肝脏。“但肝脏是很神奇的器官,具有极强的再生修复能力。我们在以往的经验中发现,急性肝衰不同于肝硬化基础上的慢性肝衰竭,如果你给肝脏一个时间足够长的‘撑住’的机会,它很可能会自己‘长回来’。”
经谨慎思考、反复论证,朱志军认为,应该给武敏的肝脏这个“机会”——将捐献肝脏一分为二,保留武敏的左半肝,辅助移植右半肝;而将捐献肝脏的左半肝移植给另一名已等待了两个多月的低体重慢性肝衰患者。他解释:一旦保留的部分自体残肝脏慢慢恢复、长大,不仅功能可以完全恢复,也可以停掉抗排异的免疫制剂,从而达到既挽救生命又避免终身服药的最佳效果。经患者家属知情同意后,朱志军决定“舍简就繁”,进行保留左半肝的辅助移植手术。
想要保证肝脏功能有机会恢复,需要在保留的残肝上留下主干血管。那么,移植手术就需要在二级分支血管上进行。要在相对更有限的空间内精准操作,并保证血管吻合后血供正常,这更考验整个团队的技术。同时,患者凝血功能的障碍也为整个手术增加了难度。朱志军说,普通的急性肝衰移植手术时长一般在4到6小时,但当天的手术一直持续了10小时。不过,手术很顺利,患者的肝功能指标在术后24小时就全部好转,48小时后患者逐渐苏醒,很快脱险出院。
经过严格的影像检查、病理活检及专业的监测评估,武敏自体的肝脏在术后第3年逐渐再生修复,开始逐步减少抗排斥药物的使用。当武敏神采奕奕地再次出现在朱志军面前时,她早就停止使用抗排斥药物了。与朱志军预判的一样,武敏的自体肝脏已完全恢复正常,达到了手术时的设计目标。
这个结果,虽在朱志军意料之中,但女孩恢复过程之顺利、状态之好,仍让他感到意外之喜。“患者和家属高兴,我们更高兴!当初为手术冒的风险和付出的心血,都是值得的!”
1998年至今,朱志军累计主刀完成肝移植手术超过3000多例,友谊医院也成为国际上最具创新活力的器官移植中心之一。2023年底,朱志军带领的友谊医院肝移植团队获得了2022年度北京科学技术奖,表彰其在“儿童肝移植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方面的成果。除了首创重塑规则的“多米诺交叉辅助肝移植”术式外,团队还在国际上率先开展多种腹腔镜微创活体供肝获取技术,以微创技术提高供者捐献的意愿。同时,开展了腹腔镜辅助下利用上腹部直切口的儿童肝移植受者手术,探索肝移植手术的微创化。
目前,友谊医院团队已完成34种遗传代谢性肝病的肝移植治疗,单中心病种数量居全国第一;儿童肝移植数量持续10年在北京地区位居第一,患者5年生存率国际领先。此外,团队完成了我国首部儿童肝移植专著,执笔、参与完成14部指南,在全国24个省(区、市)的38家三甲医院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推广应用,为我国乃至世界肝移植领域发展做出贡献。
回顾20余载来时路,一场场如履薄冰的手术历历在目,让已是国内肝移植领域顶尖专家的朱志军感慨万千。而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迎难而上的选择中,他和团队不断创新手术术式,逐步探索肝源紧缺的救命难题。
“有人问我,可曾迷茫,为何为医?我答,从不迷茫。那一张张历劫重生的笑脸,可以涤荡一切迷茫。”朱志军说。 (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微博
微博 微信
微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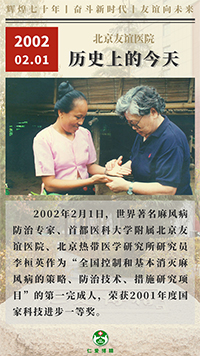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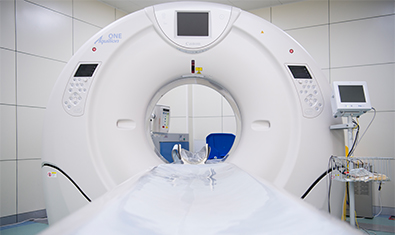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30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305号